荷兰最终改口,称可以不再接管安世半导体,只要中方满足一个条件
11月7日清晨,荷兰的风从海上吹来。那一天,政府内部传出一个转折性的消息——只要中在几天内恢复芯片供应并得到核实,荷兰就准备暂停接管安世半导体。
一夜之间,曾经的强硬口气忽然变得柔和。外界震惊,不仅因为立场逆转,更因为它来得太快。

改口与条件
11月7日清晨,海牙的天还没亮,新闻先传了出来。
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,荷兰政府准备暂停接管安世半导体,但前提是中方要在几天内恢复芯片供应,并且让荷方能核实。报道中的动词是“suspend”,也有人说是“shelve”,无论哪一个,都意味微妙。
就在一天前,安世荷兰总部还在强调“中工厂生产的产品无法保证真伪与质量标准”。前一天的质疑还在空气里回荡,第二天政府就改了口。

路透社在同一天跟进。报道中写道:“若中恢复出货,荷兰最早可能在下周暂停实施干预。”消息一出,欧洲汽车行业的采购群里立刻传开。那些焦虑了几周的生产主管开始盯着屏幕刷新闻。
荷兰经济事务部拒绝评论消息,但一名发言人表示:“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供应安全。”这句标准化的回应,没有任何温度,却泄露出一种急迫。过去几周的断供危机,终于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安世半导体总部保持沉默。网站没有更新,社交媒体也没有新声明。只有一条内部联系指令在员工间流传——继续履行合同,不做公开评论。与此同时,欧洲车企的采购部门开始重新统计库存,计划调整订单。
这场风波的转折显得突兀。10月中旬时,荷兰政府还在解释“干预合法”,强调否决权只是防范风险,如今却提出“只要供货恢复即可暂停接管”。从安全话题转向供应话题,仅隔三周。
分析师指出,这种转向背后有现实压力。欧洲多家汽车制造商已经报告关键芯片短缺,供应链中断的风险逼近临界点。政治压力让位于工业现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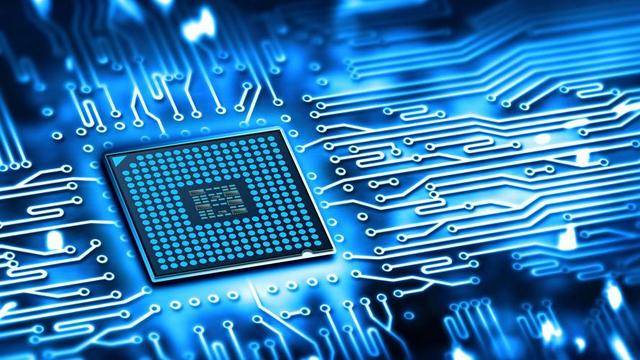
但彭博社的报道里还有一个细节,被多数人忽略。消息人士称,即便暂停接管,这一决定也不影响“中荷双方未解决的财务问题”。换句话说,政府只是暂时松手,权力并未归还。
这一让步更像是一场临时停火。政府在争取时间,企业在争取喘息。谁都明白,真正的解决还远没到。
11月7日傍晚,阿姆斯特丹的新闻频道循环播放这条消息。解说员念到“暂停”时特意放慢了语速。那一刻,整个事件的重心发生了反转——从接管到退让,从政治到供应。

秋风骤起
回到一个多月前,一切的起点在九月底。阿姆斯特丹的法院在清晨送达一份判决书,暂停了安世半导体执行董事张学政的职务。几乎同一时间,荷兰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宣布动用《商品可得性法》,对安世实施一年期“否决权”。
这部法律原本是为国家紧急物资储备设计,用于在能源危机或供应中断时让政府接管关键行业。它从未被用于针对一家外资企业。这次成为第一次。

政府的公告措辞谨慎,称这是为了“防止关键技术外流、保障供应链安全”。但在商业圈,这个理由并不被接受。公司股权没有变动,权力却被收走。这意味着,即使安世仍是闻泰科技全资控股,真正的决策不再完全由董事会掌控。
路透社在10月13日的报道中写道,荷兰此举在欧洲极为罕见。消息指出,政府可以阻止或反转公司任何关键决定,但不参与日常运营。一句“不参与”,掩盖了实质上的控制。
安世是一家有六十多年历史的芯片制造商,前身是飞利浦半导体的一部分。2019年被中国闻泰科技收购后,总部仍留在荷兰奈梅亨,员工超过一万人。多年来安稳运营,直到今年秋天突然被卷入政治漩涡。

消息传出后,行业震动。荷兰商界担心这会成为对外资的新先例。企业家组织发表声明称,若政府可以随时动用否决权,外国投资将受到影响。
安世的中国母公司保持克制。公开报道显示,中方代表多次与荷兰政府沟通,强调企业运营应当依照市场原则,不应被政治化。外交口径简短,没有情绪。
但在公司内部,气氛开始紧张。安世荷兰总部的管理层被要求重新提交一系列审批文件,包括供应协议、合同修改和投资计划。每一步都要通过政府顾问审查。行政程序放缓,外部订单开始积压。

这一连串变化迅速传导到生产端。十月初,欧洲客户陆续收到延迟通知。一些车企开始寻找替代供应商,但很快发现安世的车规级芯片几乎没有完全可替代的型号。
荷兰媒体报道,一位行业人士形容局势“像突然拧紧的阀门”。气压骤降,没人知道哪一刻会爆裂。
政府坚持称此举合法合理,称这是为了“确保关键技术安全”。可就在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区,更多人看到的是不确定。一个政府干预企业治理的先例,意味着未来的模糊边界。
十月的欧洲开始降温,新闻标题越来越冷。“荷兰政府接管中资芯片企业”——字样清晰,语气坚硬。此后的一切,都是从这里延伸。

断供的阴影
十月中旬,欧洲的供应链开始失衡。安世半导体的芯片出货速度突然下降。工厂的仓库堆满封装好的晶圆,文件在审批环节滞留。几家车企先后向荷兰政府表达担忧,称部分型号芯片已进入“关键缺口期”。
路透社报道,中境内的安世工厂在出口环节出现“个案审批”制度。这并非全面禁止,却让每一批货都要重新申请。供应商焦虑,客户更焦虑。欧洲媒体用“潜在断供”形容这一现象。

荷兰政府召开紧急会议。经济事务大臣卡雷曼斯在会后向记者强调,“政府并未干预商业决策”,但同时也承认供应情况“令人担忧”。这场新闻发布会持续不到十分钟,没有新的解决方案。
安世荷兰总部内部发布通告。文件指出,自10月13日之后在中生产的芯片“无法保证真伪与质量标准”。这句话点燃了整个行业。客户开始怀疑产品质量,供应商陷入尴尬。文件被公开后引起轩然大波。
这份通告成了风暴中心。欧洲媒体连续报道,认为荷兰方面此举或为“舆论防御”。企业客户开始要求额外认证,一些工厂暂停采购。安世在多线受压——生产停滞、客户流失、政府干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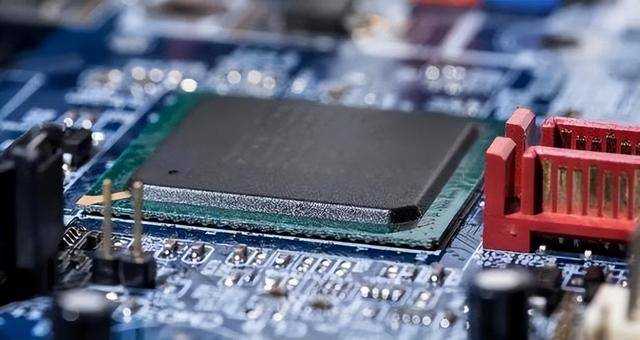
几天后,安世发布新的说明,称“公司正积极解决供应问题,并与相关部门保持沟通”。语气克制,没有任何保证。外界的耐心在消耗,内部的信任在瓦解。
欧洲汽车业的神经被彻底绷紧。生产线因为几颗芯片被迫延迟。一个看似普通的元件,成了上千台汽车无法下线的原因。断供不是抽象的危机,而是每天的现实。
到十月底,安世的产能利用率下降。工厂仍在运转,但出货量明显减少。欧洲媒体称这是“半隐性停产”。政府的干预令仍在,市场开始等待新的动作。寒气从供应链的末端一路传回海牙。

暗流未平
十一月初,局势开始出现松动。中工厂部分恢复生产,物流公司收到新的出口指令。几批货柜在上海港等待装船。欧洲客户收到发货确认,长久的静默被打破。
安世荷兰总部对外保持低调。公司声明仅一句:“继续履行客户承诺。”这十个字被多家媒体引用。没有解释,没有评论,只有延续。
荷兰政府的干预令依旧存在。文件没有撤销,否决权依然有效。这意味着公司任何重大决策仍需政府审查。外界把这种状态称作“悬置管理”——没有彻底控制,也未真正放手。

议会内部开始争论。部分议员认为政府此举破坏投资环境,应立即结束干预;另一部分则强调国家安全与供应自主权。两派在辩论中互不相让,政策陷入拉锯。
在奈梅亨的工厂,生产线重新启动。员工们按照正常节奏工作,却能感受到空气里的不安。管理层谨慎处理每一份文件,任何改动都要层层确认。公司表面平静,内部暗流涌动。
11月7日那天的“改口”,让一切重新转向。荷兰政府终于表示,只要中方恢复并核实供应,就可暂停接管。消息传出后,欧洲市场迅速反弹。车企松了一口气,芯片经销商重新启动采购。

但风波并未真正结束。暂停不等于撤销,控制权仍是隐形的枷锁。荷兰经济事务部强调,暂时的让步不涉及公司治理问题。法律层面的约束仍在生效,未来能否恢复完全自主权仍未知。
11月8日,港口的货柜被吊上船,驶向欧洲。仓库的灯重新亮起,工人开始夜班。机器声重新响起,却夹杂着谨慎。没人敢说危机已过,只知道下一个决定还在等待。

海牙的风比往常更冷。街头的灯映在运河上,光线摇晃。文件还在政府手中,权力仍未归位。安世的名字从新闻标题退到次日版面,但故事并未结束。
安世总部依旧执行命令,政府继续保持否决权。一切都恢复了,又似乎什么都没变。
参考信源:
彭博社:若中国恢复芯片供应,荷兰准备放弃对安世半导体的控制权》——路透社,2025年11月7日。
《荷兰政府接管中资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》——美联社,2025年10月13日。
《荷兰与中国就安世半导体出口管制问题展开会谈》——路透社,2025年10月17日
